

2022-04-11 阅读数:991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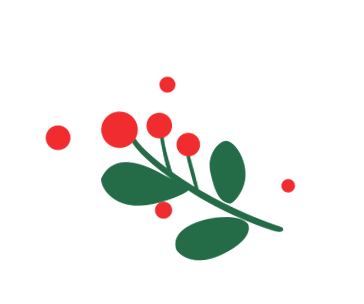
校友故事
1960年8月末的一天,我怀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情,踏入了当年新建的云南畜牧兽医学院。

从昆明乘上通车不久的贵昆铁路的简易车箱,两小时左右到达了简陋的小哨火车站。来车站迎接我们的,是彭和禄和李长生同学。他们帮我们背上行李,跨过一块低凹的山地,登上一座生长着稀疏松林的山丘,向西举目望去,前方一片稍微平整的土地上,展现出一排排兵营式的平房。他们介绍说:这就是我们的学院了。
我是调干生,来这所大学报到之前,在玉溪县人民政府秘书室工作。这是一个令人钦羡的岗位。由于读大学心切,之前的1959年秋季招生,我曾报考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,公然被录取了。只因命运不该走那条路,在通知到医院体检返回机关的县委大楼门口,正好县委常委开会结束,几位部长们簇拥着县委书记迎面而来。由于平时工作关系,其中几位较熟悉,想回避也来不及了,只有打招呼。他们问我干什么?也许是想把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张扬一下,顺口便说到医院体检。“有什么病?”“他考大学被录取了。”组织部部长代为回答。县委书记听到这句话,发怒说:“考什么大学!干部还不够安排。一个也不能动。”就这样,上大学的梦破灭了。
1960年,我在县委水利办公室工作,被指派长驻昆明,与省水利厅等部门联系水利工程机械及相关设备等事。6月中旬的一天,突然接到电话,通知我立即返回单位,要我参加高考。我怀着疑虑和兴奋的心情回到玉溪,到县委办公室找主任拿介绍信。我踏进县委办公室,主任微笑着对我说:去年不让你去,是县委书记的决定。今年通知你参加考试,是省委的通知,有条件的干部都可以参加高考。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已开好的介绍信。我接过一看,是报考云南省水利学校(中专)的。我说:“对不起,中专学校我不读。”“你要考什么?”“当然是考大学。”“那我重新给你开一张。”就这样,我终于拿到了通向高等学府的通行证。
参加高考,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历程。我当时的特长是文科和政治类。第一批录取的消息传出,我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录取。许多人都来向我祝贺,我也兴奋了一阵。可是又一次好景不长。过了十多天,传出的结论是:家庭政审不合格。
由于当年新建了许多高校,考生生源不足,尤其像畜牧兽医学院这样的大学,应届生都不愿意报考。所以又动员再考一次。最后我被录取在云南畜牧兽医学院。拿到录取通知时,打击再一次袭来。心想,读完畜牧兽医的大学回来,也无非是分到畜牧兽医站工作,哪有我现在所在单位的岗位吃得开!于是下决心不读这个大学了。当时的领导知道此事后,忙给我说:“你还是去读,先去试试吧。读一年看看,如果你觉得不好就回来。我们留给你原来的工作岗位。”这就是“试试看”的缘由。
面对兵营式的土建教室和宿舍,面对简陋的课堂桌椅和教学设备,面对刚从高校毕业分来的年轻教师和黄土堆上长满了野草的校园,开始了第一学年的大学生活。第一年,学校开设了数理化等基础课程。对我来说,也得用心和花时间去学习,开始领悟到“畜牧兽医”也并非是单纯的“医牛医马”。“试试看”的心理开始动摇了。到了第二学年,又开了有机化学、生物化学等课程。当年,全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开始改变对苏联教材一边倒的状况,开禁了一些新的课程,例如遗传学就开了《米丘林遗传学》和《孟德尔遗传学》。
《米丘林遗传学》课程结束后,紧接着准备上《孟德尔遗传学》。然而我突发眼疾,长时间住在昆明治病,没有听过一节课。逛书店是我的爱好。一天,在新华书店看到山东大学方宗煦教授编写的《细胞遗传学》。此书一到手,就再也放不下来。认真地读完全书,方知这是一门相当有价值的而且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学科。
从昆明医治眼疾回到学校,学期已告结束,正值第二学年的期末考试。考虑到我因治病未能上课的情况,学校领导通知我,不参加期末考,来年再补考。实际上,我已用治病的空闲学完了方宗煦的《细胞遗传学》,我也完全有把握参加考试。于是我向学校提出:“考试我参加,考及格了算通过,考不及格再补考。”这样就参加了全班的统一考试。结果,《遗传学》以99分的高分名列第一。由于对遗传学的偏好,我在小哨的花庄河边曾对同学立下誓言:“遗传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。我毕业以后,如果分到基层,我不会去当兽医,而是恢复我的老本行——作秘书工作。如果留学校或到 研 究 所 , 我 将 一 辈 子 从 事 动 物 遗 传 学 研究。”
毕业了,有幸留在学校工作。1965年创办云南农业劳动大学,我被派到寻甸参与劳动大学的创建。当时我曾考虑到新建的学校,可能少些框框,便于自己开创遗传学应用的科学研究和实践。1966年以后是“文化大革命”,混乱了若干年。之后,昆明农林学院与云南农业劳动大学于1970年合并。1973年恢复招生。招生后,我曾义务为农学系几个班的学生在阶梯教室补上《细胞遗传学》,并承担园艺系《普通遗传学》的教学和实验。
此时,我开始考虑作一点遗传学课题研究前的准备,于是非常关注遗传学界的科研动态。1974年,中国科大著名遗传学家杨纪珂教授在农业部举办多次猪育种讲习班,作了“杂交与近交原理”、培育近交系的意义和前景的学术报告。此后,我收集了相关文献和杨纪珂教授发表的论文集,开始了科研选题。
文献表明,美英等国从1925年后即开始进行过大规模的猪的近交系研究,但由于早期世代出现严重的近交衰退而最终归于失败。此后的50多年,遗传育种学界把猪的近交系培育视为不可逾越的科学禁区。既然是科学禁区,我为什么又要来闯这个禁区呢?首先,杨纪珂教授说,利用西双版纳小耳猪这样已有一定近交程度的地方猪种,有希望培育成功近交系。第二,也是他说的,谁如果完成一个猪的近交系选育,未来的经济价值不亚于开发一个大庆油田。对于我来说,并不想去开发一个大油田。但这个处于“科学禁区”的研究课题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。我认真分析了美英等国开展近交系研究的文献,发现他们培育近交系的技术路线是错误的。从现代遗传学理论推论,我大概可以获得成功。1977年,农业部一位猪育种技术顾问来昆明,他也对杨纪珂提出的理论感兴趣,提出希望到西双版纳进行资源考察。考察结束时,他向版纳州政府提出,应重视小耳猪的保护和研究。1979年,版纳州科委与云南农大联合向云南省科委联合申报项目。鉴于国际上没有成功的先例,他们并不同意近交系列题。我抬出了杨纪珂的大牌子,他们只好同意进行“近交观察”5年,如果没有问题再列题。就这样,经过多方寻找,终于在1980年2月14日找到了一窝适合进行近交研究的母猪和所生的仔猪,从此开始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近交系研究项目。当然,在技术路线上,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。认真作起来之后,也并非一帆风顺,头一、二代仔猪出现死亡和畸形率达90%以上。在这样的困难中又坚持了数年,终于闯过“近交观察”这一关。在此以后十多年的研究过程里,随着猪的群体逐渐扩大和研究工作的深入,取得了很大成果,也引起了不少矛盾,产生了不少争论,甚至是争吵或争夺。研究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,有人还要求近交系立即出“经济效益”。在这些形形色色矛盾斗争之中,小耳猪终于在2003年达到了国际规定的连续20个世代的高度近交,培育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近交系,并于2005年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。
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近交系培育成功了,这是值得庆幸的。要达到真正的应用还有许多路要走。到了这一步,不由得想起小哨花庄河边难忘的大学生活。

难忘小哨火车站和长满劲松的丘陵;难忘兵营式的土坯建成的教室和宿舍;难忘清亮如镜的花庄河水;难忘湖中畅游和垂钓;难忘山花和野草;难忘党委书记带领师生上山砍柴;难忘老教师带着年轻教师与学生一道成长;难忘在不起眼的山窝里,培育出了云南一批批肩挑重担的动物科学技术人才!半个世纪过去,弹指一挥间!